巴迪欧最新访谈:游牧无产者、选举政治的失败、身份认同主义
来源:2019-10-16 | 人围观
近日,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新作《内在的真理》出版,这是他继《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后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著作,自此他完成了自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花费长达四十年完成的三部曲。事实上,巴迪欧不但是理论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参与过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作为知识分子参与与工人联合的实践,这些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思考路径影响非常大。在他看来,今天法国也许已经不存在当时他所参与社会活动时代的工人阶级,因为大城市外围的工业区已经被摧毁,传统的工结构已不复存在,它们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然而,困扰着欧洲的移民问题,却是新的无产阶级,是全球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游牧无产阶级”,必须放在全球层面的阶级关系中理解。他进一步指出,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时期的殖民主义在今天的法国社会仍然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仇穆排外的刻板印象以“文明”的名义重现,表现为一种惊人的确定性,认为西方世界优于其他任何世界,西方是现代文明的解药。然而实际上,正是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结构造成了今天不可弥补的差距。谈及今天的法国政治格局,巴迪欧认为马克龙的当选与历史上路易·波拿巴和戴高乐的当选有相似处,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民众对左右翼党派都不满意,认为除了接受自称既非左翼也非右翼的马克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而在掌握权力的大资本家的影响下,选举系统本身便是有利于极右翼的。使玛丽娜·勒庞格外反动的与其说是民粹主义,不如说是她的“身份认同主义”,她的法国民族主义背后隐藏着法西斯主义。最后,巴迪欧指出,我们正处在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2月21日有力地写下《共产党宣言》时不幸所处的位置上。如今保守势力格外强大,我们需要一边反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不足,一边就当下的具体情况开展新的实验。近日,“异见者(The Dissident)”网络杂志的记者朱利安·勒格罗(Julien Le Gros)对巴迪欧进行了采访,原文于2018年12月17日发表在异见者杂志上,英文版由戴维·芬巴克(David Fernbach)翻译,载于Versoblog。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萨特追随者你的新书《内在的真理》(L’Immanences des vérités,Fayard,2018 )是一部极为丰富艰深的哲学传奇!
巴迪欧:这本书是我从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系列作品的最后一部。第一本书《主体理论》(Theory of the Subject)出版于1982年,它仍然和当时的政治有关,但也是一次新的哲学转向。之后是三部曲《存在与事件》(1988)、《世界的逻辑》(Logic of Worlds,2006),最后是《内在的真理》,它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系列的完成。
这本书中有穿插着戏剧性的段落,讲到了斯宾诺莎和柏拉图、数学理论、整数……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多学科综合的作品吗?
巴迪欧:我或许不会用这个词。哲学总是关涉一切的。它从一开始就探讨过戏剧、政治、科学……有必要把我所从事的各种活动——我是个政治活动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与哲学利用这一结合体的方式区分开来,哲学会从反思的角度看待这些自然材料。我是个多面手,并试图在哲学领域中把这些学科结合起来。
你的三部曲中出现的 “哲学家艾哈迈德(philosopher Ahmed)”是谁?他最早是在你1984的戏剧《微妙的艾哈迈德》(Ahmed le Subtil)中出现的。
巴迪欧:我那时在奥贝维利埃的戏剧公社(Thétre de la Commune)办了一个哲学研讨班。出于哲学原因我想讨论戏剧,必须让这个角色在场,不能只是引用他的话。在舞台上工作时我请来了我的朋友,导演兼演员迪迪埃·加拉斯(Didier Galas),由他扮演艾哈迈德。他表演了一些小片段。在哲学中,我们会举许多日常生活、历史或艺术中的例子。这使我能以展示而非引用的方式把例子具体化。
你在新书的“现代有限性的诗性过程”一章中,分析了勒内·夏尔(René Char),尤其是他的诗“图书馆在燃烧(La bibliothèque est en feu)”。他的作品如何启发了你?
巴迪欧:勒内·夏尔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他能把自己的政治使命“诗化”。他是抵抗运动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二战期间武装抵抗运动的成员,化名“亚历山大上尉”。通过超现实主义,他能把抗战的经历写成诗歌。他把他的一部分历史及军事经历翻译诗歌语言的能力,总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对我来说很重要。戏剧和诗歌是不受哲学的直接控制的,从我年轻时起,它们就以某种无序和存在主义的方式与我相伴。
什洛莫·桑德(Shlomo Sand)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The End of the French Intellectual, Verso,2018)中讲述了法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瓦解。作为世界上读者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
巴迪欧:实际上,近期对法国哲学的这一判断,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智识性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时期,人们把法国知识分子描绘为“坚定的(committed)”。这个形象是在法国被塑造起来的。这个国家向来是作家激进政治立场的大熔炉。不仅萨特站到了共产主义一方,战前一些作家也站到了极右翼一方:罗伯特·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法国哲学家加入了反动和保守主义的阵营。当外国人说法国智识的瓦解,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不需要这些“新哲学家”所展现的东西——这些人既不新也不是哲学家。其他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保守主义者了。他们对我们的新自由主义不感兴趣。幸运的是还有一些例外的人,可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
你也有“追随者”,比如说阿尔贝托·托斯卡诺。
巴迪欧:坚定的哲学家总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是萨特的追随者。萨特是个能吸引所有人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追随者(disciple)”是个有点麻烦的哲学概念,因为许多追随者都是未来的背叛者。
你是怎么与萨特分道扬镳的?
巴迪欧:我从来没有真的与萨特决裂。他于1980年去世时以及在那之后,我写了最后几篇关于他的文章,我向来承认他的伟大。而在哲学方面,我很早就和他分道扬镳了,20世纪50年代末,当我发现结构主义、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吉尔·德勒兹、雅克·拉康等人的新作品的时候……我就不能再从事现象学或者存在主义了。但由于萨特对他的政治使命始终坚定,在这方面我依然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没必要激烈地批评他。这更像是渐行渐远的过程,最终我的作品无疑与萨特反差很大。
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到1968
你最初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参与政治的?
巴迪欧: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对殖民冲突采取立场开始投身政治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和随后的越南战争,在动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问题上,我和萨特的立场很近。他相当积极地投身其中。当时的状况非常残酷,如今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其他的例子。但阿尔及利亚战争离法国很近,不要忘了当时有一百万年轻法国人不得不去阿尔及利亚打仗。进攻相当暴力,还使用了酷刑。十九岁时我参加了第一次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示威活动远非和平。警察用警棍之类的东西打我们。尤其因为那时我们组织得还不够好,我们还不知道必须先有一个坚实的集团,才能去示威。我们像一群羔羊走向屠宰场,也体验到了当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个世界能够多么暴力。这一经验使我坚信,任何真正的政治立场都具有一些对抗性。我们不得不与主流世界发生冲突,即使这并非义务。我认为那些奉承既定秩序的人不算是真正的哲学家。
在你看来,那时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还依然扎根在人们头脑中吗?
巴迪欧:我所有的经验都指明了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反阿拉伯、反穆斯林、排外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迅速重现的,殖民思想的浸染历史久远,依旧强盛。它仍然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表现为一种惊人的确定性,即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优于其他任何世界。显然,西方,也就是最后一批扩张主义国家,认为自己(而且西方大多数人都相信)是现代文明的万能药。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结构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差距。把在某些方面丑陋而可怕的东西等同于文明的最完美形式,是一种盲目的暴力。
2005年,你在《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法国“少数民族”遭遇的文章。在那之前,你的刚果裔养子被捕了。
巴迪欧:官方统计数据就在那里。如果你是黑人或阿拉伯人,在街上被逮捕的几率是白人的二十倍。在我们的社会中,“可敬的公民”和那些被认为不可敬的公民之间,有着事实上的隔离,有一幅外国人的相貌就足以被差别对待。这种现象不可容忍地遍及我们整个社会。
穆卢德·阿舒尔(Mouloud Achou)的“大新闻(Le Gros Journal)”(译注:法国脱口秀电视节目)播出时,你见到了阿萨·特拉奥雷(Assa Traoré)。2016年她的哥哥在佩尔桑-博蒙警察局死亡,她和阿当马委员会(Adama Committee)谴责了警方的暴力行为。工人阶级社区和你所属的特权阶级有可能建立联系吗?(译注:阿萨·特拉奥雷的哥哥阿当马·特拉奥雷在拘留所死亡。警察起初称他因饮酒和吸食大麻死于心脏病突发,并拒绝让他的家人查看尸体。第二次验尸结果则表明阿当马死于窒息。该事件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阿当马委员会旨在为阿当马事件伸张正义,他们与黄背心一起走上街头抗议。)
巴迪欧:我认为可能。这是意愿的问题。我和住在阿多马之家(Adoma Homes,供无力负担普通商品房的人居住的公共住宅)的非洲工人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过许多年,遵循他们的规则……体验他们的不幸。我和这些人相处起来没有问题,他们往往在电视上稍微了解过我。在我的政治斗争中,我交往的都是因这些不幸而动员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或者是属于这个弱势群体的人。与我一同行动的朋友和同志都来自这些地方。而我的敌人,那些经常贬低我的人,往往都是位高权重的人。
在你的《我们有权反抗》(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Fayard,2018年)一书中,你讲述了68年5月你的一次重要经历,你在兰斯教书时与当地肖森工厂(Chausson factory)的工人见了面。
巴迪欧:从感性上说,那是我在68年5月的主要经历。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原先以为分离的两个世界是能突破这种范式的。虽然我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工人阶级世界的重要性,但从生活的角度说,这与作为兰斯(Reims)的哲学教师的我相距甚远。1968年,我意识到教师可以像我们当时那样走向肖森工厂。我们渐渐地被接受了。最年轻的工人最先开始和我们说话,然后我们继续在城市里举行振奋人心的会议,参加的有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在社会活动家和学生的支持下,工厂中设立了团结基金。阶级壁垒没有妨碍我们建立起一个政治与兄弟情谊性质的项目。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始终铭记那时发生的事。
后来,你去了巴黎八大(又叫做 University of Paris-Vincennes)教书,这个地方这是思想的先驱。
巴迪欧:这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大学,从最初的1969至1971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都是一片试验田。各种政治团体在此都有体现,讲座会变成会议,一次简单的投票就能让大楼被占领。有人和警察打架,我们派代表团去工厂,我们和郊区的教师对话。有一段时间这里是滋养好战性的温床,后来又重新强调了控制与“稳定”。学校的智识经历也非同寻常,因为吉尔·德勒兹、米榭·塞荷、弗朗西斯·夏特勒和米歇尔·福柯都在这里教书。这段经历对我而言就像大学版本的兰斯的工厂经历。两者有着相互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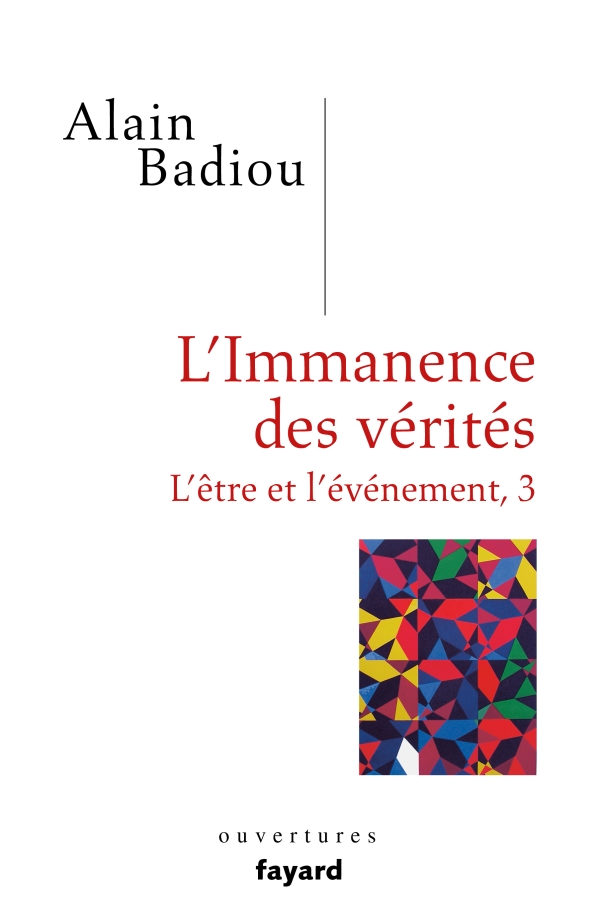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的游牧无产阶级
看到Parcoursup( 原注:最近推出并遭到质疑的在线大学申请系统,用于把候选学生匹配到“适合”的课程)的出现和“大学对所有人开放”的理念的瓦解,我们能从得出什么结论?
巴迪欧:你提到这一点很好。但可惜,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如今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实施。有两个因素导致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段长期的、极为反动的阶段,改变了局面。首先它有意识形态性质:在出现以新哲学家和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为具象的反攻之后,这种反动思想在很大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法国经历了持续的去工业化过程。我要说的是,当初我和工人们互动的那些工厂今天都已经不在了:包括兰斯和热讷维利耶的肖森工厂、塞纳河畔维特里的罗纳普朗公司(Rhne-Poulenc)、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工厂(Renault)……我们在那里建立过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核心。多年来我与这些人密切合作。那里没有出现政治的倒退,只是这些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了。大城市外围的工业区已经被摧毁。最后一点是,这个国家不再是当时那样了。“可能的政治风貌”已经改变。目前,主要问题是大规模人口流动。一个来自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游牧无产阶级已经形成,我们必须与这个无产阶级重新建立政治联系。
在难民问题上,法国左派从根本上分裂为“新反资本主义党(New Anti-capitalist Party[NPA])式的国际主义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由梅郎雄组建的政党)主张的保护主义两股阵营。你的立场是什么?
巴迪欧:如今,为了理解任何一种重大政治议题,都需要把它放入全世界的范围内。从组织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不关注这一层面,便无法了解情况。说法国已经不再有体力劳动者并非完全错误,而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工人数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过。简单来说,这些人都在中国、孟加拉、柬埔寨、巴西或者罗马尼亚。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只透过法国这个小孔来窥视政治和社会局势,便会严重误解局面。四十年前,法国有着完整的社会结构,有农民和大工厂里工作的工人。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变化迫使我们相应地改变思维方式。如果你的衡量尺度和对手不一样,你肯定会失败!如今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庞大的游牧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t),它被称做移民。事实上,这是个全球层面的阶级关系问题。它至少意味着应当优先考虑国际关系,对那些来到我们国家、希望定居在这里的游牧无产阶级形成一个立场。我喜欢意见有分歧的问题,达成共识的那些事情很少是正确的。移民问题令人困惑,造成主要的政治分歧。左派的立场并不明确。游牧无产阶级的组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先提出它。战略政治舞台是全球性的。在这点上,资本主义领先了一步,因为它是在全球舞台上自在地建立起来的。
存在着一种对68年5月的浪漫想象,它把这一事件简单地视作“道德革命”。不过,伊曼纽尔·马克龙未能把握这一事件的事实,似乎表明它仍然具有颠覆性……
巴迪欧:68事件始终有种不能被官方彻底“消化”的性质。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比其他人更坦诚一些,他说:“我们必须结束68事件!”这句话的优点是它清楚明了,它这味着对萨科齐来说,1968年还在那里,还没有被彻底清算。出于两个主要原因,这次事件对反动派来说依然是消极的标志:一方面,这场激进的经历非同寻常,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有效联结,对既定秩序来说非常危险;另一方面是道德观念的变化,如性解放,它构成一种对“坏脾气的反动派”普遍的家庭、社会保守主义构成威胁的生活方式。这一事件是不能被取消的,因此它引起了分歧。
对马克龙的消极拥护
你抵制选举。有些人说向身份政治的回退导致了美国的特朗普、巴西的博尔索纳罗(Jar Bolsonaro)当选, 2022年极右势力可能会在法国取胜,你对此有何回应。
巴迪欧:选举过程对极右势力来说一向是天赐良机,我们必须质疑它。就连1933年希特勒也是通过正常选举掌权的。我们从没见过共产主义者赢得全国选举。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当选后,这种情况仿佛真的发生了,但两年后,我们意识到这只是先前秩序的延续。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已经当选了,它还会再次当选!为什么?因为这种选举权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一种共识系统,每个人都接受它的规则。如果是这样,这便是因为它能与现有的主导秩序相符。
为什么?
巴迪欧: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一直相信选举是个自由的空间,能够决定国家的根本方向。正如密特朗当选时前信息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正确指出的那样:“选举是为了改变政府,而不是改变社会。”他说的是实话,因为这是一条大家似乎都同意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统治者——众所周知,他们是一小撮大资本家——不会接受对他们有害的选举。当情况变得太激烈、风险太大时,他们会聚集到作为最后防线的极右翼那里去。可以说,选举是共识系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其中茁壮成长。我认为选举不曾发挥过什么其他用途。唐纳德·特朗普可以在美国当选,但共产主义者不行。在各个国家都是这样。议会选举制度是由英国帝国主义发明的,它在十八世纪遭到了卢梭的批评。卢梭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选举不是民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选举系统积累了财富,采用选举系统是一个权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大程度和影响力的标志。
2015年,在奥德·兰斯林(Aude Lancelin)于Médiapart网站主持的“反潮流(Contre-courant)”节目中,你和“我们能”(Podemos,西班牙左翼政党)的国际事务主管豪尔赫·拉戈(Jorge Lago)进行了讨论。你怎么看待“我们能”运动的可持续性?
巴迪欧:他们显然完全是选举游戏中的囚徒。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经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在希腊,这个政党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执行者。直到今天,齐普拉斯(Tsipras,激进左翼联盟领袖)政府还监禁着那些活跃的激进分子。希腊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政府正在关押那些试图反对拍卖公共住房的团体,而公共住房拍卖已成为欧盟领导下的希腊资本主义最有利可图的活动。“我们能”并非无处不在,问题在于该党是否应该和社会主义党结成选举联盟。在意识形态层面,这是一场有意思的激荡,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能”仍然是主导体系的一部分。
你如何解释伊曼纽尔·马克龙在民众中的不受欢迎,与他所受到的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如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等)追捧之间的反差?
巴迪欧:我把马克龙看做是是法国独裁传统的副产品。当传统的政党制度岌岌可危且不平衡时,一个独特的人物出现,立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利用这些形势确立自己的权力。拿破仑通过军事政变结束了革命成员的内部争吵。路易·波拿巴则结束了1848年的“混乱”。面对君主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无法达成一致的状况,他“从上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戴高乐将军也有独裁的主张。
巴迪欧:正是戴高乐把二战期间完全对立的抵抗派别统一了起来。抵抗运动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他们肯定不会被允许执政。马克龙在比较小的规模上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是在左、右派同时面临危机时出现的:左翼已经瓦解,共产主义者不复存在。社会党在行使权力时已经丧尽了信誉。右翼表现不佳,因为它无法调节与极右翼的关系;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拥有大量追随者,有可能真正掌权。面对整个议会制的双重危机,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某个人组建了他的政党,他的小团体,并宣称自己“凌驾于政党之上”,就像戴高乐当时那样。马克龙首先说他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所以问题是他究竟属于哪里。我家里有许多马克龙的支持者,就像他们当初支持戴高乐或者路易·波拿巴一样,人们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拥护:如果不是他,还能是什么?只会更糟糕!
因此去年第二轮总统选举时……
巴迪欧:你必须支持马克龙,不然——可怕!——就会是玛丽娜·勒庞!在公众看来,支持马克龙基本上是一种否定,而不是拥护。他的政策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调整:必须将一切私有化,结束社会保障,像美国那样做。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看,“其他办法都是不可能的”。这正是马克龙既强大又脆弱的原因。由于他采取了行动,我们便不得不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评判他,而不只是出于“没有别的办法了”。他的措施是没完没了的一团糟,他对领养老金的人的打击困扰着他们,也困扰着养老院的护士,他只关注大城市又打击了其他省份的人,燃油税政策惹恼了黄背心们……于是人们意识到,马克龙在法国开展快速美国化的工程会使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尽管如此,他的呼吁中仍然有着消极的一面,即认为没有别的办法了。整个知识圈都说,我们既不能选马丽娜·勒庞,也不能选让-吕克·梅朗雄,他们似乎是两个极端。这很可笑,因为我看不出梅朗雄有什么极端的地方。
“民粹主义”一词的用法没有意义
媒体的话语似乎假定极左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有某种关联。乌戈·帕勒塔(Ugo Palheta)的《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 fascisme,La Découverte,2018)一书指出,这种混合实际上有利于极右翼。
巴迪欧:我觉得这些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极其奇怪。这是个在原处打转的拼合词,一个用来贴的否定标签。仅仅因为当权派指责某人是民粹主义者,并不能告诉我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它只告诉我这些人在统治系统中不受欢迎。“民粹主义”一词的用法意味着,如果你太关注民众的观点,你就会持反动的、令人不可接受的观念。这种想法很奇怪。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那些把一切他们称作极端的事物都归纳为“民粹主义”的人,似乎站在一种对人民持不信任的立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诉诸于我们共和国伟大的人民主权。这里的语义是模糊的。那么民粹主义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是一切令寡头集团不开心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心民众所说的东西吗?因为他们希望人们更加“自觉自愿”?对我来说,民粹主义一词背后藏了一些可疑的东西。
媒体称玛丽娜·勒庞是“民粹主义者”。
巴迪欧:在我看来,玛丽娜·勒庞的反动和危险不在于她是民粹主义者。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她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是“身份认同主义者”(编注:identitarian,身份认同主义运动是本世纪初发轫于欧洲多国的白人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族裔混居,强调欧洲血统的危机意识)。她的“内涵”是贝当主义的(Pétainist):工作、家庭、祖国,这与民粹主义不同。政治中对身份的崇拜总是把法西斯主义暗藏在或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形式中。它总是基于身份,却不是人民的身份。人民总是包含许多不同的身份。我们应该抛弃“民粹主义”这个词,明确地说出我们究竟为什么批判这个或那个倾向。玛丽娜·勒庞诉诸于一种完全神秘的法国身份,而法国这个国家的身份是无法描述的。另一方面,如果极左人士讨论主权和人民利益,就让他们说吧,为何不呢?这是它的传统。我们也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民粹主义者。梅朗雄则没那么危险。
你和雅克·朗西埃的演讲都卖空了。你认为在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
巴迪欧: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处在全球性的反革命阶段。保守势力不仅完全从属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它还想废除之前取得的成就。共产党一度很强大,其中有着坚定、革命性的知识分子。马克龙正采取攻势,系统地击垮这些俘虏。他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这种打算的人。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正试图根除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孤零零的进步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指明另一条道路的阵营必须做到清晰。形势不利。我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重头开始的阶段。
你认为我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上?
巴迪欧:几乎就在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2月21日有力地写下《共产党宣言》时不幸所处的位置上。那时能代表他所描述的共产党的几乎就只有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今天的首要任务是意识形态和实验性的:有没有能让我们尝试与主导秩序公开对抗的新模式的政治议题?在法国,有“游牧无产阶级”的问题——我不用“移民”这个词,因为这并非他们的身份。冲突存在,起步阶段总是这样,事情正混乱地开展着。政治实验,必须与对马克思主义的仔细、长期且系统的检查关联起来,也需要和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尝试联系起来。彼得格勒和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成就、哪些不足?怎样的组织能让我们避免这些工作的失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把从具体情况出发的实验,与对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成就与不足的大规模集体考察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立即着手做这件事。
最后,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项目吗?
巴迪欧:我正处在一个不太明确的时期。我可以对自己说,81岁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唯一的问题是,这不符合我的秉性。在哲学建构方面,我感觉我已经无法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了。我的三部曲是完整的系列。我可以从事个别的研究,比如实数,但这些活动都局限在很特定的领域内。作为一个老人,我想写一本传记——不是个人传记,而是政治传记。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法国和马克龙的法国之间有一丝联系。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你讲述这两个阶段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在第四共和国末期、殖民事件期间进入政界是怎样的?以及之后我参与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68年五月风暴和毛派的经历……还有当前的形势。人们似乎对这个有兴趣。
相关内容推荐:
- 2026-02-12比美国还嚣张的国家出现,禁止所有中国外交官入境,不让统一
- 2026-02-02临阵脱逃,高市早苗辩论前突然“手伤”
- 2026-01-31省纪委督办批转南阳纪委立案不查敷衍扯皮
- 2025-12-03北京“无事不扰”企业总量已突破55万户
- 2025-12-02金昌:构建梯度培育体系 激活中小企业发展动能
- 2025-09-2423家企业斩获9项大奖
- 2025-09-09一份来自中国企业的可持续行动宣言
- 2025-08-20安全泛化侵蚀美科技企业竞争力根基
- 2025-08-05从三家外贸企业看发展韧性
- 2025-07-03“职”等你来 193家企业携1.3万余个岗位亮相银川
- 推荐阅读
- 话题列表
-